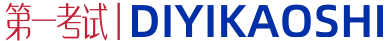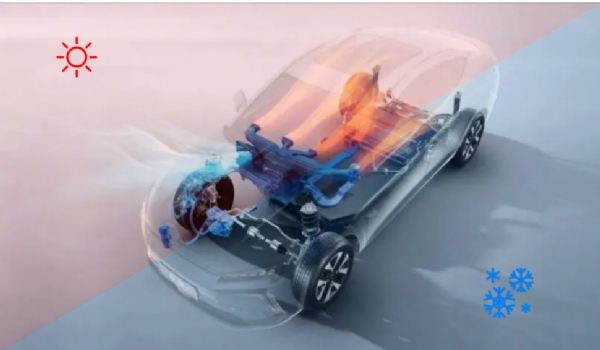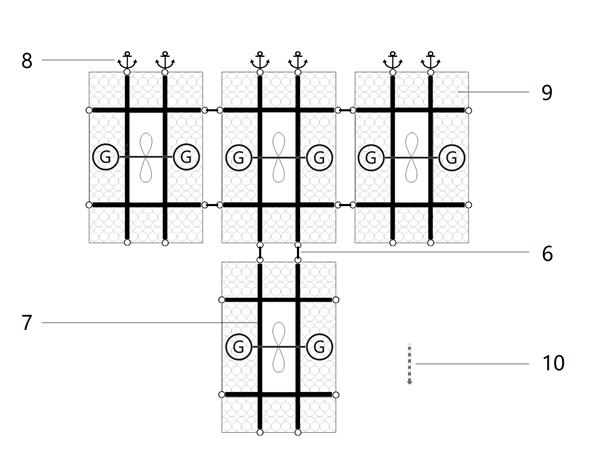周轶君:《他乡的童年》不是中国家长的教育终极答案,但我们依然可以给孩子更多可能
周轶君:《他乡的童年》不是中国家长的教育终极答案,但我们依然可以给孩子更多可能
\\n
看点
《他乡的童年》曾一度打开了许多家长的教育观,如今第二季又带来了新加坡、德国、法国、泰国、新西兰五个国家的体验。在看到其他国家的教育时,我们不禁也想问:中国家长能从中看到什么?学到什么?理想的教育只存在于他乡吗?
本文转载自公众号:童书妈妈三川玲 (ID: tongshuchubanmama)
采访 | 白滔滔 记录整理 | 贾嘉
图片编辑 | 林郁 排版丨Luna
五年前,我周围的教育工作者、家长,几乎在同一时间,开始频繁提到一个名字,叫做《他乡的童年》。
我刚开始以为是一本记录一个在他乡成长的童年回忆录;随着热议程度直线上升,我开始一集一集地一口气追着看完,才发觉这是一部在全球寻找真正的教育的纪录片。
深为震撼!
日本、芬兰、印度、英国和以色列,最后,回到中国。六集,六段旅程,也是六段叩问。
我想,即便作为专业的教育研究者,校长,也很难有机会如此深入广博地去全世界探寻教育,更不用说普通家长了。
作为教育、媒体行业加起来20多年工作经历的我,深知,这个事情量有多大,难度有多大,价值有多大。
2020年,2021年,2022年,2023年,2024年……
时隔五年,当我看到周轶君老师在朋友圈里说《他乡的童年》第二季终于在优酷上线的时候,我有一种老友重逢的冲动和感慨。
短短的五年,恍若隔世。
尤其,是这一两年来,躺平、凝滞、反复、倒退;认真做事的人,越来越少,逃避寻求安稳的人,越来越多;就算努力做事,很多时候,也会有一种空拳打出去的无力感。
由此,我更加敬佩,这个时代,还在坚持独立思考和追寻本质和真相的人。我觉得,这才是这个世界有可能变得更好的希望。
作为“希望”,周轶君并不那么沉重,反而,有一种泰然的平静。
因为,每个国家、每种文化之下的教育,都是不同的;
这个世界上,并不存在一种绝对的“完美的教育”,有的,就是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生活的地方,自己的家庭里,可以做什么。如此而已。
《他乡的童年》日本篇
一位幼儿园园长写的孟子“不为也,非不能也。”
一问,你为什么要跟教育死磕?
周轶君笑了:我没有死磕(我还做了环保题材的《碳路森林》纪录片呢)。《他乡的童年》就是第一季做了,很自然地接着做第二季。
我自己对教育有困惑、有思考,想着大家或许也是一样,那么,就去多看看,多问问。
二问,你说,要从教育哲学看待每个国家、每种文化下的教育形态,那么,你自己的,或者说,你认可的教育哲学是什么?
周轶君回答:
教育,就是让人成为人。像人的样子活着,像人的样子学习和成长。
三问周轶君:你在走过那么多国家,观察过那么多教育模式之后,觉得中国教育最应该补的课是什么?
周轶君的答案,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:
玩的课,生活的课,哲学的课
。如果要抽象概括一下,就是
“身体自由成长+精神自由绽放”
。
又替一位家长问,“他乡”,是我们要去追随的目的地吗?我已经从中国来到了新西兰,我应该去新加坡吗?
周轶君提醒大家:
他乡,不是目的地,只是镜子。
作为中国家长,我们并不必要“将他乡做故乡”,我们只需要看到:
教育从来不只一种面貌;生命有无限的可能。
且让我们,慢慢道来。
怕输的是孩子,还是父母
在新加坡著名精英学校——南洋小学门口,周轶君跟几个刚放学的小学六年级学生聊天。
她问:你们班里有多少同学?孩子们说:38。
她又问:有多少人能考上重点中学?有人说:一两个。也有人说:五六个。
《他乡的童年》新加坡篇
墙面上规划完整的时间表
小学下午两点钟放学,但孩子们不能放松神经。他们要补课,每个人都有好几个补习班要上。
在中国语境里,大家提到“一考定终身”,第一反应往往是高考。最近由于“普职分流”,中考的重要性又被大大提高。
但在新加坡,小学六年级就是分水岭。
周轶君敏锐地感知到,
若是六年级就有了命运分界线,那么孩子们的起跑点一定远远低于六年级,也许从一年级,不,从幼儿园,不,从出生时住在哪一所房子开始。
南洋学校的学区,曾经是从学校中心向外辐射一公里,但2021年政策变了,学区是从学校围墙向外辐射一公里,带来的效应,是新近划入学区的房子,瞬间总价又涨了几十万甚至百万。
看过《他乡的童年》第一季的观众们,曾经跟着周轶君领略过了许多让人向往的教育模板,并一字一句地记录心得。
但是,到了《他乡的童年》第二季第一集,新加坡的教育战争,足以让屏幕前拿着小本本的手发出共振的抖动。弹幕里说:补课已进入华人的基因。
《他乡的童年》新加坡篇
当地升学制度图解
在新加坡的一家补习班里,墙上那句
“I\\\'m not here to be average, I\\\'m here to be awesome”(我来这里不是要成为普通人,我来这里是要成为优秀的人)
分外扎心。
沉重,是父母豪掷千万买学区房的经济压力,是补习班孩子书包的重量,是新加坡年轻人自杀率的数字,也是这个岛国几十年来的求生求存欲
。这个国度不服输,这个国度里的每一个人心里,都被植入了一个“思想钢印”:怕输。
在新西兰,周轶君听到了一个与新加坡的价值观截然相反的故事:
一个学生以“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”为主题写了一篇文章,但却被他的老师打了零分——老师问他:什么是人上人?人人都是平等的,为什么要做人上人,你要把谁踩在脚下?
孩子的价值观,往往来自父母,或者来自环境。
当人才被看做国家兴衰的关键,就诞生了Meritocracy(中译为“精英主义”),机会和奖励都会以“才能”为基础进行分配。
可问题是:
社会仅仅需要“精英”吗?
再进一步的问题是:
能够通过这套机制筛选出来的,是什么样的“精英”?
或许,我们谁都没有答案;但是,我们不能不由此开始思考。
很多问题的来源,都是没有玩好
在中国,孩子特别缺哪门课?
周轶君第一个答案是:
玩的课,“我觉得很多问题都是没玩好。”
在《他乡的童年》系列中,没有哪个地区的孩子,像新西兰的孩子那么能玩,会玩。
这里的孩子,从小就要学会跟海洋亲密接触,从会走路就开始下海。
《他乡的童年》新西兰篇
正在海里玩耍的孩子们
在奥克兰一所小学里,孩子们有长达35分钟的课间玩闹时间,他们可以在不受任何干涉的情况下,在“无法无天操场”上自由选择玩耍方式,秋千、拔河、爬树、上房顶、从斜坡上滚下去……
有家长机智地发现了一个细节,在弹幕区写到:一个戴眼镜的孩子都没有。
周轶君问校长:不设任何玩耍规则,不担心孩子们受伤吗?
校长说,有规则的时候,孩子们也经常摔断胳膊摔断腿,随他们去玩。
周轶君:父母通常认为,孩子无法在安全问题上管好自己,我们必须提供保护。
校长:
如果我们一直提供保护,他们永远学不会。
周轶君:有父母会来抱怨吗?
校长:
Never。
新西兰校园里,孩子们玩耍的画面,是《他乡的童年》第二季最令人难忘的场景,
那种肆意的探索,发自内心的笑容,以及呼朋唤友的热闹,展现出的是人类天性中对自由的热爱。
《他乡的童年》新西兰篇
而且更令人动容的是,孩子们在疯玩的时候也会互相提醒——挥舞棍子时要小心,不要砸到人。他们还会主动清理路上的大树枝,以防有人会被绊倒。
节目上线后,周轶君曾回忆在新西兰这家学校的感触,她觉得自己“受到了教育”,无论作为节目制作者,或是作为家长,都学到了很多,“我一进去就疯了。”
她会想起,在德国拍摄的时候,听一个朋友讲过,某家学校门口有两棵特殊的树——专门让孩子们爬的树。孩子爬得越高,就证明风险承受能力越强。
虽然这个细节没能出现在纪录片里,但是新西兰那个矫捷爬树的小女生,让她找到了画面感。
在中国的城市里,孩子“玩耍”的空间总是被层层压缩。
首先,家长们会害怕危险,对于孩子在学校里的任何磕磕碰碰如临大敌;
其次,学校因为害怕惹事担责,所以并不会给孩子真正“疯玩”的时间与空间;
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,正如周轶君在节目中发出的“天问”:
为什么最先被舍弃的,都是玩耍的时间?
但是在新西兰,周轶君了解到,早在十三年前,这家“疯玩”学校的前任校长就做过一个为期两年的实验,让孩子们不受限制地玩耍。结果表明,这种对“学习时间”的挤占,不但没有影响孩子们的学习效率,反而能极大地提升孩子的专注力,甚至还减少了校园霸凌。
《他乡的童年》新西兰篇
周轶君坦言,自己作为家长,在考察了新西兰教育之后也会深受影响,也会考虑如何把限制孩子们的东西拿掉,让孩子自己去决定安全边界在哪里,基准线在哪里,找到属于自己的东西,属于自己真正的兴趣,从“玩耍”中慢慢发现自己的兴趣点。
兴趣是最好的老师,这句话经过了无数次检验。
在芬兰,《愤怒的小鸟》制作人在和周轶君聊天时,就曾引用中国先哲孔子的名言,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,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”。同样在在芬兰,一位老师说,“哪怕我们中某个孩子不擅长数学或者科学,又不擅长艺术,但他们依然能发现自己的力量。”
周轶君想起,在《他乡的童年》英国篇,她采访威斯敏斯特公学校长,向对方问起:招生面试时会问什么样的问题。
那位校长的回答是:What is your passion(你的兴趣是什么)?
有些事,上大学才懂就晚了
在《他乡的童年》日本篇,有一家叫“藤”的幼儿园,园如其名,主打一个让孩子们亲近自然,爬树,养马,种菜。
园长曾经对周轶君说过一句话,让她至今印象深刻:
如果到20岁才知道真正的洋葱长什么样子,就太晚了
。
《他乡的童年》日本篇
这是“藤”幼儿园的圆形操场
在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里,读书种子“四体不勤,五谷不分”并不总是贬义。
中国家长在督促孩子学习时,总有一种什么都“放着我来”的大包大揽精神——快要高考了,备考是天下第一件重要的事,家里什么事你都不要管。
但这种大包大揽,结果却是把孩子与真实的生活隔离。孩子们成功考上了大学,脑子里填满了各种各样的知识,但却处理不了生活中某个具体的小事儿。
所以,
周轶君对于“中国孩子最应该补的课”这个问题,给出的第二个答案是:真实的生活
。
但她补充说,生活需要开课来学吗?不需要的。
在《他乡的童年》法国篇中,有一个非常挑战人们固有认知的细节:幼儿园的孩子们学着自己吃饭时,用的刀叉餐具,都是成人尺寸,而不是特制的儿童尺寸。
而在新西兰的幼儿园,更加令人震惊,孩子们会学着使用锤子,把木板上翘起来的钉子锤进去——小家伙执着地寻找着所有“越位”的钉子,锤了一个又一个,最后还不忘把锤子还给园长。
在日本、以色列、德国,周轶君都看到过学会了“使用工具”的孩子。
在新西兰,周轶君跟一个来自辽宁的小女孩聊天。小女生落落大方,侃侃而谈自己的梦想,说起学习成绩,也有一种我们熟悉的自豪,但说到自己不擅长的课,她说起了做饭——她太不敢用刀具——“炒菜我也得用个刀,我也不敢呐”。
“学习是为了回到生活,回到环境。”
这也是《他乡的童年》芬兰篇的点题金句。
芬兰、新西兰、德国的教育,有一个共同的社会底色,就是一个人是否受到社会尊重与他的职业并不会深度绑定——大学教授的社会地位并不比蓝领工人高,论工资可能还不如水管工,建筑工,电工等专业人士。
《他乡的童年》德国篇
关于社会价值观的一段采访
“不是只有学习成绩好的人,才能成为社会上有价值的一员”。
周轶君在剑桥大学读书时,曾经听到一位老师自黑说——你知道在象牙塔里教书的都是什么人吗?都是社会的loser(失败者)。
后来她偶然认识的一位资深投资人朋友也曾吐槽说:别迷信藤校的毕业生,他们除了学校那套话以外别无长处。
周轶君发现,迷信,或者成见,无处不在。
教育的目的,如果只是名校、爬藤、好工作、高工资、社会地位这些具体而实际的东西,那么随着时代变化,总会有巨大的风险横亘在面前。
学历会贬值,好工作神话会破灭,社会地位永远都是相对的,能拿到高薪的群体也会随着产业而转移,那么,还剩什么是永恒不灭的?
周轶君曾采访过很多艺术家,也曾感动于他们肯为了梦想与追求而穷尽一生之力,并为所在的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。
但现在她也会想:是艺术家成就是艺术,还是艺术这件事拯救了艺术家的一生?如果没有找到这件事,这些人的一生会如何度过?
真正的逻辑也许是这样:
是某个具体的事,让一个人的一生有所寄托。
我们问起周轶君:你的教育哲学是什么,对自己的孩子期待是什么?
她的答案是:
成为一个精神上不匮乏的人。因为精神不匮乏这件事,是能够支撑着人过一辈子的。
只有精神丰盈的人,才能穿越任何时代周期
。
家长能为孩子做的最好的事
周轶君曾感慨说:我走过了那么多地方,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地方的父母,像中国父母那样,可以为教育付出那么多。所谓,可怜中国父母心。
可是,她从另一个角度看——
家长又是妄念与梦想的集合体
。
这种妄念或者梦想,在《他乡的童年》新加坡篇中可能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每个父母都觉得自己的孩子是天才,很难有人接受孩子只是一个“普通人”。
父母们从孩子一出生就在这个小生命上投射了许多期待,望子成龙望女成凤,“孩子的成长有他自己的逻辑,但我们家长做的很多事,只不过是满足自己的妄念和梦想。”
周轶君提到,在《他乡的童年》泰国篇中,有父母带着孩子去留学,但并没有和孩子事先商量这件事,孩子在到达目的地之前,一直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旅行,怎么也没想到他从此要在那里上学。这件事对孩子的精神伤害很大。
我们问周轶君,她在体验了那么多的教育后,
觉得最好的家庭教育有什么共同的特点
。
周轶君的回答是:
尊重孩子
。
这是一个如此朴实简单的道理,但太多人做不到。
周轶君觉得,这种“尊重”的极致状态,她在法国就看到了——在法国教育哲学里,婴儿是一个完整的、独立的、需要被平等对待的个体。法国的护士在给新生儿换尿片时,都会跟孩子说话。法国的育儿者会努力“理解”幼儿的身体语言,推测他们的意图和需要。
有一个法国式的共识:一个人的心理问题可以追溯到0到3岁的时候。
就如纪录片中所说,
“法国人的教育是关于生活,关于生而为人的感受,它始于对婴儿的理解,启迪儿童的思辨。”
《他乡的童年》法国篇
现在,周轶君经常会给刚生孩子的朋友建议,当孩子幼小的时候,一定要跟孩子多说话,不停地说。
当孩子长大一些后,父母就要少说话,少指挥,千万不要把孩子自主性拿走,不要让孩子习惯于靠别人来做决定。
不要总是催孩子什么时候该洗脸刷牙,什么时候必须上床睡觉,也不要总是在房间里溜达去看孩子在干什么,要尊重孩子长大成人的愿望。
她有一个观察:
往往家长能力越强,孩子能力越弱。所以,“在你可控的环境里少管点。”
如果家长总觉得孩子没长大,要帮他做所有事,替他做所有事,那么孩子或者变成了牵线木偶,或者会导向逆反的方向。
在以色列,周轶君遇到过一位教育界人士,他给孩子设定了一个规矩:几点睡觉这件事你可以自己决定,但前提是手机和电脑不可以带进卧室,在睡觉前一个小时不可以打游戏。
周轶君也遇到过要不要让孩子打游戏的纠结,从她自己的角度看,第一反应是希望孩子不要碰游戏,但是她会反思——要不要因为自己对游戏的不了解和不喜欢而强制孩子服从。
她跟朋友交流这件事,有朋友说:父母能为孩子做的最好的事是不要给他手机。
但是,她又会想到另一个事实:很多孩子在没有手机的环境下长大,但在考上大学后,报复性地疯狂玩游戏。
作为一个在严格的家教下长大的孩子,周轶君经常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,“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后退一步”。
孩子想试着做饭做蛋糕,她会放手让孩子去厨房摆弄刀具和点火,只提一个要求是自己要打扫好战场。孩子把锅碗瓢盆都拿出来,当成打击乐器来玩,她也听之任之,只要不过分扰民。
在孩子的成长中,家长能做什么呢?
周轶君觉得,
家长能对孩子做的最好的事,也是最难的事,就是真正客观地去观察这个孩子
。
《他乡的童年》日本篇
因为,教育没有标准,孩子也不是一个模子套出来的。每个孩子都不一样——哪怕是亲兄弟姐妹或双胞胎,也有着巨大的差异性。只有认真观察,了解孩子的个性,才能知道孩子适配什么样的教养方式。
这是父母的功课,一门经常被忽视的功课。
让孩子玩,让孩子与自己相处,让孩子无聊,让孩子做决定……这都是家长的观察时间。只是,别急着下结论,就像一位法国幼教所说,
孩子都是会变的,童年只是一个漫长故事的开端。
可能性的价值
周轶君曾听到某位父亲说,自己尽管经济能力很强,但绝不对把孩子送到国外学习,理由是:如果孩子在外边接受了别的价值观,就跟自己想法不一样了。
这个观念让周轶君有点吃惊,她会觉得:为什么一定要让孩子的价值观和自己一致?
但是,她同时又抑制住了自己评论的冲动,因为她并不熟悉这位父亲,也没见过他的孩子,她不觉得自己有资格或有能力去对这个决定做出评判。
在周轶君的概念里,
教育,可以是一个国家或社会层面的公共事务,但同时也是一个家庭内部私域事务。
发生在私域里的教育,只要不违反法律和底线(比如不能有家暴),旁人无法越俎代庖。
一个家庭选择什么样的教育方式,就是由家长的三观决定的。
但家长的观念是不是能传递给孩子,这取决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。
比如很多人会反感强势的棍棒教育虎妈爸,但在现实中,一个天才儿童真的有可能在强势霸道的父亲威压下成人成名。
教育还有一个特点,就是没有绝对正确的“宝典”
。饶是像周轶君这样”见多识广”的家长,也会在亲子教育上小小横跳几下。当孩子越界时,她也会发火,也会觉得应该拿出点权威来——但是,这与尊重孩子不矛盾,“尊重孩子的同时也要放过自己”。
在新加坡,周轶君见到过专门“体罚”孩子的藤条。卖藤条的小店老板对她说:打孩子这事,主要是为了疏解家长的压力。
在藤条店里拍摄时,周轶君还跟一位在新加坡长大的英国女生聊了几句,那位女生没有入镜,她只是对周轶君说:我不相信暴力。
这句话让周轶君发现:
也许在一个家庭里,孩子的觉醒与抗争,也是成长的一部分
。
比起用语言或体罚让孩子服从,周轶君注意到,有一个更有效的方法——“父母的潜意识对孩子的影响,比你显性的行为(说的话、做的动作)影响要大得多。”
这就像是“暗物质”,不可见,但能量巨大。
做父母的一个细微的表情或微不足道的小动作,在孩子眼里会被放大很多倍。比如,幼小的孩子咬手指的动作,往往源于父母的焦虑——尽管这种焦虑被有意识地掩藏过,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,但是,“父母在孩子面前,什么都装不了”。
所以,有句话说,“鸡娃不如鸡自己”。
《他乡的童年》芬兰篇
周轶君拍《他乡的童年》,最希望改变的也不是孩子,而是教育孩子的人——家长,老师,学校,社会。
为什么很多家长会逼着孩子去学习,去追逐名校、名利?因为家长的成长过程中并没有亲身感知过人生的其他可能性。自己没有体验过的东西,又怎么可能传递给孩子?
而《他乡的童年》能做到的,恰恰就是作为一面镜子,照出各种可能性。
这种可能性,也许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体验得到,但是,
作为家长来说,了解更多的可能性,意味着对孩子未来的选择,多一些理解和宽容。
这是人人都能做到的。
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补上哲学的课?
因为理解的前提是沟通,而沟通的前提,则是双方对同一个概念有共识——《他乡的童年》法国篇的故事证明,哲学能帮我们做到这一点。
哲学,实在是太重要了——正如复旦哲学教授王德峰所说,中国的教育,如果不进行哲学层面的思考和构建,在现有的技术层面上的调整,是改不好的。
我们从全世界的不同的教育现象所能带来的最好的结果,就是我们一起来思考,到底什么是我们最好的教育。
如此,善莫大焉。
(原文有删减)
关注外滩教育
发现优质教育
\\n
看点
《他乡的童年》曾一度打开了许多家长的教育观,如今第二季又带来了新加坡、德国、法国、泰国、新西兰五个国家的体验。在看到其他国家的教育时,我们不禁也想问:中国家长能从中看到什么?学到什么?理想的教育只存在于他乡吗?
本文转载自公众号:童书妈妈三川玲 (ID: tongshuchubanmama)
采访 | 白滔滔 记录整理 | 贾嘉
图片编辑 | 林郁 排版丨Luna
五年前,我周围的教育工作者、家长,几乎在同一时间,开始频繁提到一个名字,叫做《他乡的童年》。
我刚开始以为是一本记录一个在他乡成长的童年回忆录;随着热议程度直线上升,我开始一集一集地一口气追着看完,才发觉这是一部在全球寻找真正的教育的纪录片。
深为震撼!
日本、芬兰、印度、英国和以色列,最后,回到中国。六集,六段旅程,也是六段叩问。
我想,即便作为专业的教育研究者,校长,也很难有机会如此深入广博地去全世界探寻教育,更不用说普通家长了。
作为教育、媒体行业加起来20多年工作经历的我,深知,这个事情量有多大,难度有多大,价值有多大。
2020年,2021年,2022年,2023年,2024年……
时隔五年,当我看到周轶君老师在朋友圈里说《他乡的童年》第二季终于在优酷上线的时候,我有一种老友重逢的冲动和感慨。
短短的五年,恍若隔世。
尤其,是这一两年来,躺平、凝滞、反复、倒退;认真做事的人,越来越少,逃避寻求安稳的人,越来越多;就算努力做事,很多时候,也会有一种空拳打出去的无力感。
由此,我更加敬佩,这个时代,还在坚持独立思考和追寻本质和真相的人。我觉得,这才是这个世界有可能变得更好的希望。
作为“希望”,周轶君并不那么沉重,反而,有一种泰然的平静。
因为,每个国家、每种文化之下的教育,都是不同的;
这个世界上,并不存在一种绝对的“完美的教育”,有的,就是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生活的地方,自己的家庭里,可以做什么。如此而已。
《他乡的童年》日本篇
一位幼儿园园长写的孟子“不为也,非不能也。”
一问,你为什么要跟教育死磕?
周轶君笑了:我没有死磕(我还做了环保题材的《碳路森林》纪录片呢)。《他乡的童年》就是第一季做了,很自然地接着做第二季。
我自己对教育有困惑、有思考,想着大家或许也是一样,那么,就去多看看,多问问。
二问,你说,要从教育哲学看待每个国家、每种文化下的教育形态,那么,你自己的,或者说,你认可的教育哲学是什么?
周轶君回答:
教育,就是让人成为人。像人的样子活着,像人的样子学习和成长。
三问周轶君:你在走过那么多国家,观察过那么多教育模式之后,觉得中国教育最应该补的课是什么?
周轶君的答案,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:
玩的课,生活的课,哲学的课
。如果要抽象概括一下,就是
“身体自由成长+精神自由绽放”
。
又替一位家长问,“他乡”,是我们要去追随的目的地吗?我已经从中国来到了新西兰,我应该去新加坡吗?
周轶君提醒大家:
他乡,不是目的地,只是镜子。
作为中国家长,我们并不必要“将他乡做故乡”,我们只需要看到:
教育从来不只一种面貌;生命有无限的可能。
且让我们,慢慢道来。
怕输的是孩子,还是父母
在新加坡著名精英学校——南洋小学门口,周轶君跟几个刚放学的小学六年级学生聊天。
她问:你们班里有多少同学?孩子们说:38。
她又问:有多少人能考上重点中学?有人说:一两个。也有人说:五六个。
《他乡的童年》新加坡篇
墙面上规划完整的时间表
小学下午两点钟放学,但孩子们不能放松神经。他们要补课,每个人都有好几个补习班要上。
在中国语境里,大家提到“一考定终身”,第一反应往往是高考。最近由于“普职分流”,中考的重要性又被大大提高。
但在新加坡,小学六年级就是分水岭。
周轶君敏锐地感知到,
若是六年级就有了命运分界线,那么孩子们的起跑点一定远远低于六年级,也许从一年级,不,从幼儿园,不,从出生时住在哪一所房子开始。
南洋学校的学区,曾经是从学校中心向外辐射一公里,但2021年政策变了,学区是从学校围墙向外辐射一公里,带来的效应,是新近划入学区的房子,瞬间总价又涨了几十万甚至百万。
看过《他乡的童年》第一季的观众们,曾经跟着周轶君领略过了许多让人向往的教育模板,并一字一句地记录心得。
但是,到了《他乡的童年》第二季第一集,新加坡的教育战争,足以让屏幕前拿着小本本的手发出共振的抖动。弹幕里说:补课已进入华人的基因。
《他乡的童年》新加坡篇
当地升学制度图解
在新加坡的一家补习班里,墙上那句
“I\\\'m not here to be average, I\\\'m here to be awesome”(我来这里不是要成为普通人,我来这里是要成为优秀的人)
分外扎心。
沉重,是父母豪掷千万买学区房的经济压力,是补习班孩子书包的重量,是新加坡年轻人自杀率的数字,也是这个岛国几十年来的求生求存欲
。这个国度不服输,这个国度里的每一个人心里,都被植入了一个“思想钢印”:怕输。
在新西兰,周轶君听到了一个与新加坡的价值观截然相反的故事:
一个学生以“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”为主题写了一篇文章,但却被他的老师打了零分——老师问他:什么是人上人?人人都是平等的,为什么要做人上人,你要把谁踩在脚下?
孩子的价值观,往往来自父母,或者来自环境。
当人才被看做国家兴衰的关键,就诞生了Meritocracy(中译为“精英主义”),机会和奖励都会以“才能”为基础进行分配。
可问题是:
社会仅仅需要“精英”吗?
再进一步的问题是:
能够通过这套机制筛选出来的,是什么样的“精英”?
或许,我们谁都没有答案;但是,我们不能不由此开始思考。
很多问题的来源,都是没有玩好
在中国,孩子特别缺哪门课?
周轶君第一个答案是:
玩的课,“我觉得很多问题都是没玩好。”
在《他乡的童年》系列中,没有哪个地区的孩子,像新西兰的孩子那么能玩,会玩。
这里的孩子,从小就要学会跟海洋亲密接触,从会走路就开始下海。
《他乡的童年》新西兰篇
正在海里玩耍的孩子们
在奥克兰一所小学里,孩子们有长达35分钟的课间玩闹时间,他们可以在不受任何干涉的情况下,在“无法无天操场”上自由选择玩耍方式,秋千、拔河、爬树、上房顶、从斜坡上滚下去……
有家长机智地发现了一个细节,在弹幕区写到:一个戴眼镜的孩子都没有。
周轶君问校长:不设任何玩耍规则,不担心孩子们受伤吗?
校长说,有规则的时候,孩子们也经常摔断胳膊摔断腿,随他们去玩。
周轶君:父母通常认为,孩子无法在安全问题上管好自己,我们必须提供保护。
校长:
如果我们一直提供保护,他们永远学不会。
周轶君:有父母会来抱怨吗?
校长:
Never。
新西兰校园里,孩子们玩耍的画面,是《他乡的童年》第二季最令人难忘的场景,
那种肆意的探索,发自内心的笑容,以及呼朋唤友的热闹,展现出的是人类天性中对自由的热爱。
《他乡的童年》新西兰篇
而且更令人动容的是,孩子们在疯玩的时候也会互相提醒——挥舞棍子时要小心,不要砸到人。他们还会主动清理路上的大树枝,以防有人会被绊倒。
节目上线后,周轶君曾回忆在新西兰这家学校的感触,她觉得自己“受到了教育”,无论作为节目制作者,或是作为家长,都学到了很多,“我一进去就疯了。”
她会想起,在德国拍摄的时候,听一个朋友讲过,某家学校门口有两棵特殊的树——专门让孩子们爬的树。孩子爬得越高,就证明风险承受能力越强。
虽然这个细节没能出现在纪录片里,但是新西兰那个矫捷爬树的小女生,让她找到了画面感。
在中国的城市里,孩子“玩耍”的空间总是被层层压缩。
首先,家长们会害怕危险,对于孩子在学校里的任何磕磕碰碰如临大敌;
其次,学校因为害怕惹事担责,所以并不会给孩子真正“疯玩”的时间与空间;
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,正如周轶君在节目中发出的“天问”:
为什么最先被舍弃的,都是玩耍的时间?
但是在新西兰,周轶君了解到,早在十三年前,这家“疯玩”学校的前任校长就做过一个为期两年的实验,让孩子们不受限制地玩耍。结果表明,这种对“学习时间”的挤占,不但没有影响孩子们的学习效率,反而能极大地提升孩子的专注力,甚至还减少了校园霸凌。
《他乡的童年》新西兰篇
周轶君坦言,自己作为家长,在考察了新西兰教育之后也会深受影响,也会考虑如何把限制孩子们的东西拿掉,让孩子自己去决定安全边界在哪里,基准线在哪里,找到属于自己的东西,属于自己真正的兴趣,从“玩耍”中慢慢发现自己的兴趣点。
兴趣是最好的老师,这句话经过了无数次检验。
在芬兰,《愤怒的小鸟》制作人在和周轶君聊天时,就曾引用中国先哲孔子的名言,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,好之者不如乐之者”。同样在在芬兰,一位老师说,“哪怕我们中某个孩子不擅长数学或者科学,又不擅长艺术,但他们依然能发现自己的力量。”
周轶君想起,在《他乡的童年》英国篇,她采访威斯敏斯特公学校长,向对方问起:招生面试时会问什么样的问题。
那位校长的回答是:What is your passion(你的兴趣是什么)?
有些事,上大学才懂就晚了
在《他乡的童年》日本篇,有一家叫“藤”的幼儿园,园如其名,主打一个让孩子们亲近自然,爬树,养马,种菜。
园长曾经对周轶君说过一句话,让她至今印象深刻:
如果到20岁才知道真正的洋葱长什么样子,就太晚了
。
《他乡的童年》日本篇
这是“藤”幼儿园的圆形操场
在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里,读书种子“四体不勤,五谷不分”并不总是贬义。
中国家长在督促孩子学习时,总有一种什么都“放着我来”的大包大揽精神——快要高考了,备考是天下第一件重要的事,家里什么事你都不要管。
但这种大包大揽,结果却是把孩子与真实的生活隔离。孩子们成功考上了大学,脑子里填满了各种各样的知识,但却处理不了生活中某个具体的小事儿。
所以,
周轶君对于“中国孩子最应该补的课”这个问题,给出的第二个答案是:真实的生活
。
但她补充说,生活需要开课来学吗?不需要的。
在《他乡的童年》法国篇中,有一个非常挑战人们固有认知的细节:幼儿园的孩子们学着自己吃饭时,用的刀叉餐具,都是成人尺寸,而不是特制的儿童尺寸。
而在新西兰的幼儿园,更加令人震惊,孩子们会学着使用锤子,把木板上翘起来的钉子锤进去——小家伙执着地寻找着所有“越位”的钉子,锤了一个又一个,最后还不忘把锤子还给园长。
在日本、以色列、德国,周轶君都看到过学会了“使用工具”的孩子。
在新西兰,周轶君跟一个来自辽宁的小女孩聊天。小女生落落大方,侃侃而谈自己的梦想,说起学习成绩,也有一种我们熟悉的自豪,但说到自己不擅长的课,她说起了做饭——她太不敢用刀具——“炒菜我也得用个刀,我也不敢呐”。
“学习是为了回到生活,回到环境。”
这也是《他乡的童年》芬兰篇的点题金句。
芬兰、新西兰、德国的教育,有一个共同的社会底色,就是一个人是否受到社会尊重与他的职业并不会深度绑定——大学教授的社会地位并不比蓝领工人高,论工资可能还不如水管工,建筑工,电工等专业人士。
《他乡的童年》德国篇
关于社会价值观的一段采访
“不是只有学习成绩好的人,才能成为社会上有价值的一员”。
周轶君在剑桥大学读书时,曾经听到一位老师自黑说——你知道在象牙塔里教书的都是什么人吗?都是社会的loser(失败者)。
后来她偶然认识的一位资深投资人朋友也曾吐槽说:别迷信藤校的毕业生,他们除了学校那套话以外别无长处。
周轶君发现,迷信,或者成见,无处不在。
教育的目的,如果只是名校、爬藤、好工作、高工资、社会地位这些具体而实际的东西,那么随着时代变化,总会有巨大的风险横亘在面前。
学历会贬值,好工作神话会破灭,社会地位永远都是相对的,能拿到高薪的群体也会随着产业而转移,那么,还剩什么是永恒不灭的?
周轶君曾采访过很多艺术家,也曾感动于他们肯为了梦想与追求而穷尽一生之力,并为所在的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。
但现在她也会想:是艺术家成就是艺术,还是艺术这件事拯救了艺术家的一生?如果没有找到这件事,这些人的一生会如何度过?
真正的逻辑也许是这样:
是某个具体的事,让一个人的一生有所寄托。
我们问起周轶君:你的教育哲学是什么,对自己的孩子期待是什么?
她的答案是:
成为一个精神上不匮乏的人。因为精神不匮乏这件事,是能够支撑着人过一辈子的。
只有精神丰盈的人,才能穿越任何时代周期
。
家长能为孩子做的最好的事
周轶君曾感慨说:我走过了那么多地方,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地方的父母,像中国父母那样,可以为教育付出那么多。所谓,可怜中国父母心。
可是,她从另一个角度看——
家长又是妄念与梦想的集合体
。
这种妄念或者梦想,在《他乡的童年》新加坡篇中可能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每个父母都觉得自己的孩子是天才,很难有人接受孩子只是一个“普通人”。
父母们从孩子一出生就在这个小生命上投射了许多期待,望子成龙望女成凤,“孩子的成长有他自己的逻辑,但我们家长做的很多事,只不过是满足自己的妄念和梦想。”
周轶君提到,在《他乡的童年》泰国篇中,有父母带着孩子去留学,但并没有和孩子事先商量这件事,孩子在到达目的地之前,一直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旅行,怎么也没想到他从此要在那里上学。这件事对孩子的精神伤害很大。
我们问周轶君,她在体验了那么多的教育后,
觉得最好的家庭教育有什么共同的特点
。
周轶君的回答是:
尊重孩子
。
这是一个如此朴实简单的道理,但太多人做不到。
周轶君觉得,这种“尊重”的极致状态,她在法国就看到了——在法国教育哲学里,婴儿是一个完整的、独立的、需要被平等对待的个体。法国的护士在给新生儿换尿片时,都会跟孩子说话。法国的育儿者会努力“理解”幼儿的身体语言,推测他们的意图和需要。
有一个法国式的共识:一个人的心理问题可以追溯到0到3岁的时候。
就如纪录片中所说,
“法国人的教育是关于生活,关于生而为人的感受,它始于对婴儿的理解,启迪儿童的思辨。”
《他乡的童年》法国篇
现在,周轶君经常会给刚生孩子的朋友建议,当孩子幼小的时候,一定要跟孩子多说话,不停地说。
当孩子长大一些后,父母就要少说话,少指挥,千万不要把孩子自主性拿走,不要让孩子习惯于靠别人来做决定。
不要总是催孩子什么时候该洗脸刷牙,什么时候必须上床睡觉,也不要总是在房间里溜达去看孩子在干什么,要尊重孩子长大成人的愿望。
她有一个观察:
往往家长能力越强,孩子能力越弱。所以,“在你可控的环境里少管点。”
如果家长总觉得孩子没长大,要帮他做所有事,替他做所有事,那么孩子或者变成了牵线木偶,或者会导向逆反的方向。
在以色列,周轶君遇到过一位教育界人士,他给孩子设定了一个规矩:几点睡觉这件事你可以自己决定,但前提是手机和电脑不可以带进卧室,在睡觉前一个小时不可以打游戏。
周轶君也遇到过要不要让孩子打游戏的纠结,从她自己的角度看,第一反应是希望孩子不要碰游戏,但是她会反思——要不要因为自己对游戏的不了解和不喜欢而强制孩子服从。
她跟朋友交流这件事,有朋友说:父母能为孩子做的最好的事是不要给他手机。
但是,她又会想到另一个事实:很多孩子在没有手机的环境下长大,但在考上大学后,报复性地疯狂玩游戏。
作为一个在严格的家教下长大的孩子,周轶君经常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,“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后退一步”。
孩子想试着做饭做蛋糕,她会放手让孩子去厨房摆弄刀具和点火,只提一个要求是自己要打扫好战场。孩子把锅碗瓢盆都拿出来,当成打击乐器来玩,她也听之任之,只要不过分扰民。
在孩子的成长中,家长能做什么呢?
周轶君觉得,
家长能对孩子做的最好的事,也是最难的事,就是真正客观地去观察这个孩子
。
《他乡的童年》日本篇
因为,教育没有标准,孩子也不是一个模子套出来的。每个孩子都不一样——哪怕是亲兄弟姐妹或双胞胎,也有着巨大的差异性。只有认真观察,了解孩子的个性,才能知道孩子适配什么样的教养方式。
这是父母的功课,一门经常被忽视的功课。
让孩子玩,让孩子与自己相处,让孩子无聊,让孩子做决定……这都是家长的观察时间。只是,别急着下结论,就像一位法国幼教所说,
孩子都是会变的,童年只是一个漫长故事的开端。
可能性的价值
周轶君曾听到某位父亲说,自己尽管经济能力很强,但绝不对把孩子送到国外学习,理由是:如果孩子在外边接受了别的价值观,就跟自己想法不一样了。
这个观念让周轶君有点吃惊,她会觉得:为什么一定要让孩子的价值观和自己一致?
但是,她同时又抑制住了自己评论的冲动,因为她并不熟悉这位父亲,也没见过他的孩子,她不觉得自己有资格或有能力去对这个决定做出评判。
在周轶君的概念里,
教育,可以是一个国家或社会层面的公共事务,但同时也是一个家庭内部私域事务。
发生在私域里的教育,只要不违反法律和底线(比如不能有家暴),旁人无法越俎代庖。
一个家庭选择什么样的教育方式,就是由家长的三观决定的。
但家长的观念是不是能传递给孩子,这取决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。
比如很多人会反感强势的棍棒教育虎妈爸,但在现实中,一个天才儿童真的有可能在强势霸道的父亲威压下成人成名。
教育还有一个特点,就是没有绝对正确的“宝典”
。饶是像周轶君这样”见多识广”的家长,也会在亲子教育上小小横跳几下。当孩子越界时,她也会发火,也会觉得应该拿出点权威来——但是,这与尊重孩子不矛盾,“尊重孩子的同时也要放过自己”。
在新加坡,周轶君见到过专门“体罚”孩子的藤条。卖藤条的小店老板对她说:打孩子这事,主要是为了疏解家长的压力。
在藤条店里拍摄时,周轶君还跟一位在新加坡长大的英国女生聊了几句,那位女生没有入镜,她只是对周轶君说:我不相信暴力。
这句话让周轶君发现:
也许在一个家庭里,孩子的觉醒与抗争,也是成长的一部分
。
比起用语言或体罚让孩子服从,周轶君注意到,有一个更有效的方法——“父母的潜意识对孩子的影响,比你显性的行为(说的话、做的动作)影响要大得多。”
这就像是“暗物质”,不可见,但能量巨大。
做父母的一个细微的表情或微不足道的小动作,在孩子眼里会被放大很多倍。比如,幼小的孩子咬手指的动作,往往源于父母的焦虑——尽管这种焦虑被有意识地掩藏过,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,但是,“父母在孩子面前,什么都装不了”。
所以,有句话说,“鸡娃不如鸡自己”。
《他乡的童年》芬兰篇
周轶君拍《他乡的童年》,最希望改变的也不是孩子,而是教育孩子的人——家长,老师,学校,社会。
为什么很多家长会逼着孩子去学习,去追逐名校、名利?因为家长的成长过程中并没有亲身感知过人生的其他可能性。自己没有体验过的东西,又怎么可能传递给孩子?
而《他乡的童年》能做到的,恰恰就是作为一面镜子,照出各种可能性。
这种可能性,也许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体验得到,但是,
作为家长来说,了解更多的可能性,意味着对孩子未来的选择,多一些理解和宽容。
这是人人都能做到的。
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补上哲学的课?
因为理解的前提是沟通,而沟通的前提,则是双方对同一个概念有共识——《他乡的童年》法国篇的故事证明,哲学能帮我们做到这一点。
哲学,实在是太重要了——正如复旦哲学教授王德峰所说,中国的教育,如果不进行哲学层面的思考和构建,在现有的技术层面上的调整,是改不好的。
我们从全世界的不同的教育现象所能带来的最好的结果,就是我们一起来思考,到底什么是我们最好的教育。
如此,善莫大焉。
(原文有删减)
关注外滩教育
发现优质教育
\\n
*本文作者,由_合作伙伴_授权发布,转载请联系原出处。如内容、图片有任何版权问题,请联系_处理。
相关领域的投资人
猜你喜欢
月内热榜
- 1 女老师穿“紧身衣”,被校长批评后很委屈:教师不能自由穿衣吗?
- 2 2022年广州41所学校高考成绩情况如何?
- 3 广东省最年轻省委常委走红,双非毕业也能身居高位,真是不简单
- 4 2023年英语四六级考试时间一般是几月份?
- 5 二十大机构改革,有哪些单位会消失,机关的你有危机感吗
- 6 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登录入口浙江:https://jiaoshi.zjedu.gov.cn/
- 7 3到10岁的脑筋急转弯五篇
- 8 2024绵阳一诊定了,四川首次大考,绵阳外的大部分学校也会参加
- 9 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登录入口广东:https://jiaoshi.gdedu.gov.cn/
- 10 实心球运动会加油稿十篇